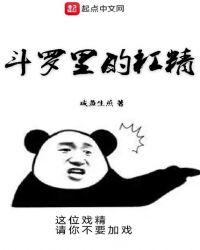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碎却圆六(第1页)
辗眼寒声碎,鬓先白,十一月连下几场雪,进十二月里,反倒日日晴光,恍有春绿之势。
何家丧事刚治完没几日,赶上何盏手头那桩盐税的案子正要了结,忙得他成日天不亮出去,天黑了才归家。便以此为由,说怕惊扰了父母安歇,吩咐人将后廊上两间屋子收拾出来搬过去住。
他母亲听见,向何齐连哭了两夜说:“媳妇才没了,他就搬到那冷冷清清的屋子去住,跟前拢共就两个丫头服侍。成日关着门不做声,除了他衙门里的事情,什么都不管不顾。我就这一个儿子,倘或看着他如此沉郁下去,作坏了身子,叫我往后靠谁?”
何齐心里亦有些烦恼记挂,父子二人自陶家抄家后,一向不曾好言好语说话。他暗里打算着,儿子虽不孝,近日却遭此悲劫,少不得是他拉下做老子的脸面,先去低个头。
这夜云澹星疏,何盏在灯下看书,听见屋檐上薄霜化水,砸了一滴下来,琤琮一声,像是由过去里响彻回来。他向着绮窗看,一看便看住了。
直到何齐进门,吭吭咳了两声。何盏方回转神,抬眼见何齐剪着手落到榻上,他便只好放下书,不冷不热地在榻下作揖。
如今何盏清瘦了几分,留着须髯,眼睛褪脱稚气,凛冽许多,仿佛出鞘的刀,不经意地冒着银晃晃的寒光,立在屋内,愈显君子遗风。
何齐将其冷眼打量一番,心内唏嘘,面上却端着老子的架子丢不开,“媳妇没了,阖家心痛,你母亲更是日夜担忧你的身子,你倒把我们避得远远的,搬到这屋里来睡,愈发叫她忧心。人早晚有一死,她死了,未必你就不活了?还该打起精神来,落后再续一房妻室,日子一样要过下去。”
不知那句点着了何盏的痛处,竟拂袖侧过身去,抬着下颌冷笑了一声。
他这一笑,怄得何齐一拳拍在炕桌上,“你搬到这后廊上,说是怕打扰我与你母亲,实则是心里还记恨我!你以为我不晓得,媳妇这病,你只想着是因陶家的事情生出来的,陶家的事,又是我办的,你心里找不着怨处,只好把你老子恨着!”
何盏乜回眼,胡子遮着唇,像是笑了,看不清,“难为父亲竟还记得这些事。绿蟾在世时,不曾抱怨过您一句,可我日日对着她,时时刻刻都觉得对不住她。却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心里可曾有一点过意不去?”
何齐心里的火一顶,噌地拔座起来,颤着手将他指着,“好啊,你果然是怨恨我。我心里过不过意的去?好,我不防告诉你,你老子不是那么没良心的人!当初陶知行的事,我原没有这个打算,自己亲家,一门子亲戚,我犯不着要想踩着他神官发财!这可是你那位至交好友席大人出的主意!”
一席话将何盏惊转回来,有些难置信。
话说到此,何齐想着索性将脏水一股脑泼在外人身上,总好过他父子二人结下终身仇怨。
因此是非曲直,便由他微妙精巧地处理了一番,“当初上呈朝廷的罪案上,我只能那么写!林戴文与席泠都在打他主意,倘或交给他们去写,重笔一落,陶知行当时就会没命!你岳父流放,殊不知我在里头斡旋多少,你还有脸怨我?!”
何盏呆怔一会,渐渐剪起手,笑意逞强,仍有些不肯信,“绿蟾没了,陶家业已家破人亡,眼下就剩两个孤儿寡母,父亲还有什么不敢认的?还要把这盆污水往别人身上泼,难道也是觉得有些良心有愧?”
“放肆!”何齐跌坐回榻,手颤颤巍巍地垂下来,搭在膝上。落后一会,他乜兮兮地笑了,“好啊,我生你养你一场,倒不如个席泠,你一门心思肯信他,却不信你老子。你天生愚钝,怎么不想想,要不是他在其中拿主意,定下大局,林戴文怎么会信他?你不防再细想想,若他干干净净,怎么一下从个九品县丞一跃为四品府丞。依你的想法,他是靠一身才华,哼,别招我好笑,若只靠才学,早几年他何至于遭那些冷遇?”
屋里突兀地静下来,只得炭盆里噼啪绽放的火花,东一下西一下地在何盏脑子里炸着。
他早该去想,或许他早该想到,但他一向刻意回避着,不敢将席泠往深了想。想深了,这世上难免什么事都经不住推敲。
沉默中,何齐叹息着擦过他的身,“你天生愚钝,至纯至诚,可这世道与你想的不一样,你老子与你的想的也不一样,就连你的至交,也与你想的有些出入。我一直不忍告诉你,今番却不得不说给你听,我儿,从前教导你的那些,原没错,可有一点忘了告诉你——你不能奢望世事都如你想的一样好,总要给世俗人留点余地。”
何齐走后,下起雨,不大不小的雨点子胡乱打在廊外那些常绿的叶丛里,天色底下,芳翠成了遍地的暗影。何盏在门首站了良久,目断处,晦暗濛濛,连一抹月痕也不分明。
云翳轻蔽月,雨只小半个时辰便落停了,夜天虽渐清,烟雾却越聚越浓,廊下的灯与芭蕉在水雾中更难分明。
丫头走进卧房,搓着手欲待阖窗,露浓却在铺上出声止住,“别关,开着吧。”
她裹着映木槿花的华褥,只露着一张迷蒙白皙的脸看着窗外发呆,目光也如星罩雾,亮得不清晰。一切在她眼里,都逐渐不分明,她想着席泠与那位神出鬼没的相公,两个人在她心里,也同样边境不明。
丫头稍稍抱怨着,“这样大冷的天,开着窗,姑娘也不怕吹病了。”
一行走到床沿坐着,对着床前的熏笼烤手,“方才我听见说,老爷回信了,说是皇上叫这里一个什么盐税亏空的案子搅了心情,一连发了好几日的火,招赘泠官人的事情,因此就不大好提。老爷传话告诉老太爷,说是等过了元宵,开了春,那桩案子了结报到京,皇上听见心情好了,那时候再说。姑娘耐着性子再等等,横竖也没听见冷官人与箫娘办喜酒的事情。上回他分明说秋天就要办的,都快到年关了还没办,想必是他心里,也在掂度这桩事。”
冰冷的风吹在露浓脸上,仍旧难拂开她心里的浓雾。席泠于她,是个绮丽的梦,可那位相公,却像个更捉摸不定的幻影,她实在难抉择。检算起来,她连他姓甚名谁尚且不明朗呢。
于是次日在船上,露浓歪着眼琢磨他,再度试问:“你到底叫什么,打哪里来?家中是做什么的?”
蔡淮解下蓑衣斗笠,露出底下穿的鸦青素锦圆领袍,不以为意地落到榻上,呷了口热茶,“你猜猜看。”
“我猜不准。”露浓笑笑,在炕桌上支颐着细窥他,跃跃欲试,“你穿的都是好料子的衣裳,手上连个粗茧也没有,成日都装作船夫在这船上。嗯……我想,你一定不缺钱使,又通文墨,必定是富贵人家的公子。你口里没有北方口音,南京话却讲得不地道,必定不是南京人,或许是附近哪个州府的富贵人氏。”
“大致不错。”蔡淮支起一条膝,歪在榻上看她。其实她没他所想的那么愚蠢,只是缺乏些实际的见识。但她又与寻常的闺阁小姐有些不同,她比她们,似乎更多一些冒险的慾望与勇气。
这是十分难得的,大多数女人都向往着一世富贵安稳。她却似玫瑰,惑人的颜色下长着不规矩的暗刺。他兴致盎然地抬手托着她的下颌,凑去亲了一下,“我单名一个淮字。”他没退开,又继续亲她,黏黏地四片唇在离合中迷得意乱。
悄无声息地,他一手将炕桌推在一边,揿着她倒下去。终于到这一步,露浓既害怕,又期待,她忐忑不安地将双手轻抵在他胸膛,“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叫什么,我是谁?”
蔡淮悬在她脸上,目光散漫得不受拘束,手拂着她的额线,“不大想知道。我有过很多女人,现在大多都想不起她们的姓名了,就是知道你叫什么你是谁也没意义,说不定明天我就不记得。”
这话倒有几分真心,他是被迫才知道她的姓名,其实抛闪那些“阴谋”,他根本无谓她叫什么,或是谁。只要此刻,他的身体是诚实的。
可这些话,到底有些不中听。露浓推开他,坐起身来,抱紧自己的双膝。她生怕不抱紧,自己就会沉溺在这种迷人的微小的心痛里。
蔡淮在旁边躺了片刻,也懒洋洋地爬起来,“得,我不勉强你,这种事,姑娘家总是怕一些的。”
他站起来,连体谅都没有半点无奈,仿佛从头至尾都对她无所谓,潇洒地整拂衣袍,伸手取榻侧高几上的蓑衣。
大明:我爹是朱元璋
defaultlongrec...
斗罗里的杠精
我不是唐三,我是唐三杠,杠天杠地杠众生。诸葛神弩?,来看看我这把满配M4,暴雨梨花针?我这高爆手雷不香吗?佛怒唐莲?不会做,但是我有小型核弹要不要…卫星射线与黎明之锤正在天空待命,随时可以摧毁所有武魂殿。...
今天开始当掌门
一无所有的逗比无忌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稀里糊涂的变成了掌门,用他行走两个世界的能力让没落的门派重新回到自己的巅峰之上...
综穿之孟婆来碗汤
很多人大概都向往过穿越重生,但是在一次次带着记忆的死去又活来之后,姜秦疲惫极了。记忆太过沉重,不论爱与恨着的人,一切都留不住。女主没有系统,没有异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不太聪明的现代姑娘第一世恶毒女配的自我救赎第一个故事脱胎于看过的一本小说,记不得名字了)第二世浔阳梁氏之寿终正寝(甄嬛传)第三世步步惊心之大清福晋的尊严第四世十里桃花之第一女战神写到哪里算哪里吧。计划十世,有时候有cp,有时候没有。...
年代文女配不干了
化学博士叶姝凝在末世来临时被陨石砸中穿越到了一本她看过的年代文里,成了书中男主的炮灰前妻。她只想远离男主一个人在这个和平安稳的世界过自己的小日子,再带着她的化学研究所发展一下自己的事业ampquot...
从一把剑开始杀戮进化
从一把剑开始杀戮进化穿越成为了一把剑!?杀戮获得进化点,从一把破剑开始,成为一把传说史诗魔剑!...